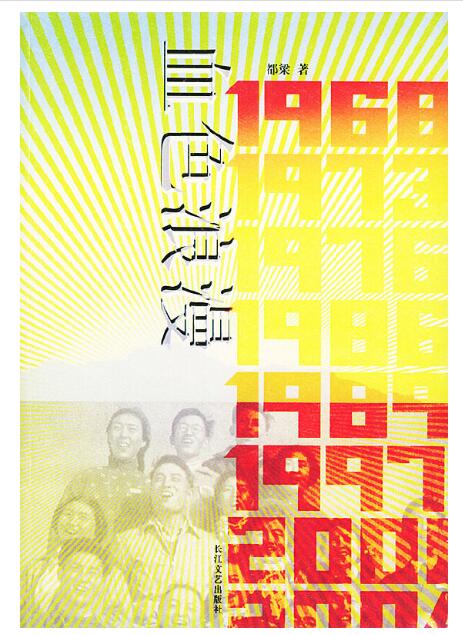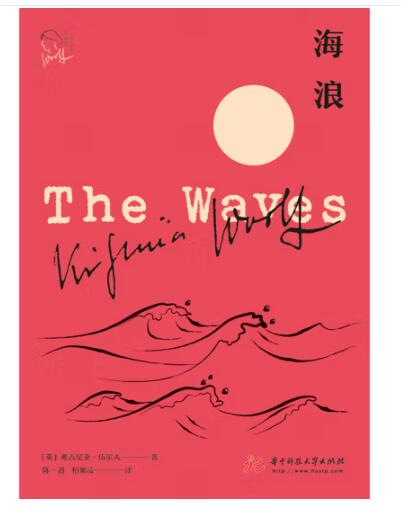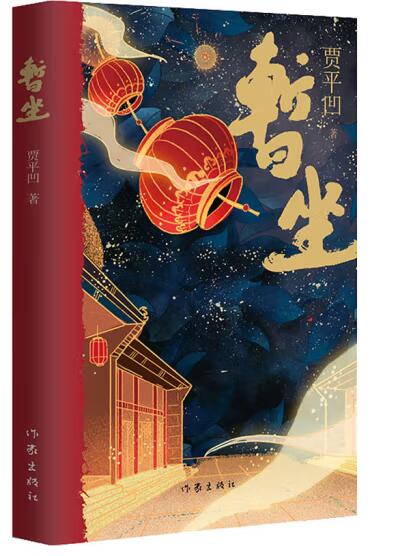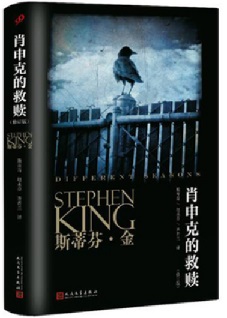内容推荐
《群山之巅》是著名作家迟子建暌违五年之后,最新长篇小说。写作历时两年,是呕心沥血、大气磅礴之作。
这部小说比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更苍茫雄浑,比《白雪乌鸦》更跌宕精彩。
小说分“斩马刀”、“制碑人”、“龙山之翼”、“两双手”、“白马月光”、“生长的声音”、“追捕”、“格罗江英雄曲”、“从黑夜到白天”、“旧货
节”、“肾源”、“暴风雪”、“毛边纸船坞”、“花老爷洞”、“黑珍珠”、“土地祠”等十七章,笔触如史诗般波澜壮阔,却又诗意而抒情。
中国
北方苍茫的龙山之翼,一个叫龙盏的小镇,屠夫辛七杂、能预知生死的精灵“小仙”安雪儿、击毙犯人的法警安平、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、绣娘、金素袖等,一个个
身世性情迥异的小人物,在群山之巅各自的滚滚红尘中浮沉,爱与被爱,逃亡与复仇,他们在诡异与未知的命运中努力寻找出路;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,努力
活出人的尊严,觅寻爱的幽暗之火……
“写完《群山之巅》,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,而是愁肠百结,仍想倾诉。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
物,而是因着某种风景,比如滔天的大雪,不离不弃的日月,亘古的河流和山峦。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,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!所以写到结尾那
句:‘一世界的鹅毛大雪,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’,我的心是颤抖的。”
——迟子建
作者简介
迟子建,女,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。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。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,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。1983年
开始写作,已发表以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,出版有八十余部单行本。主要作品有:长篇小说《伪满洲国》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《白雪
乌鸦》,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《白雪的墓园》《向着白夜旅行》《逝川》《清水洗尘》《雾月牛栏》《踏着月光的行板》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,散文随笔集《伤
怀之美》《我的世界下雪了》等。出版有《迟子建长篇小说系列》六卷、《迟子建文集》四卷、《迟子建中篇小说集》五卷、《迟子建短篇小说集》四卷以及三卷本
的《迟子建作品精华》。曾获得第一、第二、第四届鲁迅文学奖,第七届茅盾文学奖,澳大利亚“悬念句子文学奖”等文学奖。作品有英、法、日、意、韩等海外译
本。
后记
每个故事都有回忆
二00一
年八月下旬,我和爱人下乡,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村庄,遇见一位老人。我在当年的日记中这样记载:“进得一户农家,见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,他衣衫破烂,家
徒四壁,坐在一块木板上,望着他家菜园尽头苍茫的黑龙江水······他对我说他是攻打四平的老战士,负伤时断了三根肋骨,丢了半叶肺,至今肺部还有两片
弹片未取出来。他说文革时他挨批斗,揍他的人说,别人打江山都成烈士了,你能活着回来,肯定是个逃兵!老人说到此气得直哆嗦。他说政府每月只给他一百多块
的补助,连饭都不够吃,前几天他刚赊了一袋米回来。老人的儿媳埋怨老人这种状况无人关照,前两年有记者来访,走后也是不了了之。我觉得很悲凉,一个打江山
的人,是不该落得如此下场的。我给了他一点钱,他坚决不收,说毛主席教导我们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我说这只是让你买袋米的钱,他这才泪汪汪地收下。”
我
还记得从那儿回来后,我爱人联系这座村庄所属县域的领导朋友,请他们了解和关注一下老人的事情。不久后他还跟我说,事情有了进展。可是八个月后,他在归乡
途中遭遇车祸,与我永别!与爱人相关的人和事,在那个冰冷的春天,也就苍凉地定格了!直到几年前,我听说某驻军部队的一名年轻战士,因陪首长的客人,在游
玩时溺亡,最终却被宣传成一个救落水百姓的英雄,这个故事,唤醒了我对那位老人的记忆,也唤醒了我沉淀着的一些小说素材。
爱人不在了的这十二年来,每到隆冬和盛夏时节,我依然会回到给我带来美好,也带来伤痛的故乡,那里还有我挚爱的亲人,还有我无比钟情的大自然!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新规,在故乡施行所引发的震荡,我都能深切感受到。
比
如火葬场的建立,在它开工之初,很多老人就开始琢磨着死了。因为那里的风俗,七十岁以上的老人,大都为自己备下了一口木棺材,而火葬场的烟囱一旦冒烟,他
们故去,就不能带棺材上路了。我还记得火葬新规是那年十月一日生效的,在此之前,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,对那些濒临死亡的老人做了普查,告知亲属,凡是死在
这个日期之后的,必须火葬,棺材要么自己处理掉,要么上缴,统一焚毁。我姐夫的母亲,由于心肺功能严重衰竭,昏迷多日,仅靠氧气维持微弱的生命。医生都以
为她活不过九月的,家人也为她打下棺材,可她却顽强地挺到十月一号,成为那座小城火葬的第一人。只因多活了一天,她的棺材只得劈了,作为烧柴,让儿女们痛
心不已!那天送她的人很多,人们都围着焚尸炉转,想看看它是怎么烧人的,因为那儿也是他们最终的去处啊。活过那个日子的老人们,对有朝一日会被装进骨灰盒
充满恐惧。我外婆在世时,提起火葬就咋舌,埋怨自己活得长,不能带着棺材去见我外祖父了。
处
决死刑犯改为注射死亡法,在老百姓中也引发了不少的议论。有人说,杀人偿命不用吞枪子了,死刑犯死得舒服了,是不是杀人的罪犯就会多了?我知道在山间法场
发生的故事,即将消失,在回乡过年时,特意去采访老法警,他们讲述的那些裹挟在死亡中的温暖故事,令人动容。我母亲当时还冲我撇嘴,说大过年的,采访杀人
的事做什么?
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,它所产生的故事,可以说是用卷扬机输送出来的,量大,新鲜,高频率,持之不休。我在故乡积累的文学素材,与我见过的“逃兵”和耳闻的“英雄”传说融合,形成了《群山之巅》的主体风貌。
对这样一部描写当下,而又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纠葛的作品,哪种形式进入更适合呢?我想到了倒叙,就是每个章节都有回忆,这样方便我讲故事,也便于读者阅读。
闯
入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,很多是有来历的,比如安雪儿。离我童年生活的小镇不远的一个山村,就有这样一个侏儒。她每次出现在我们小镇,就是孩子们的节日。不
管她去谁家,我们都跑去看。她五六岁孩子般的身高,却有一张成熟的脸,说着大人话,令我们讶异,把她当成了天外来客!她后来嫁了人,生了孩子。我曾在少年
小说《热鸟》中,以她为蓝本,勾勒了一个精灵般的女孩。也许那时还年轻,我把她写得纤尘不染,有点天使化了。其实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,而是凡人的欢笑和
眼泪,所以在《群山之巅》中,我让她从云端精灵,回归滚滚红尘,弥补了这个遗憾。
再
比如辛七杂。在我们小城,有个卖菜的老头,我们家一直买他种的菜。有年春天他来我家,问我们想要多少土豆、白菜和萝卜做越冬蔬菜,他下种的时候,心里好有
个数。他肤色黝黑,留着胡子,裤子和鞋上尽是泥,但面目洁净。那天太阳好,他站在院子里,说着说着话,忽然从腰间抽出烟斗,又从裤兜摸出一面凸透镜,照向
太阳,然后从另一个裤兜抽出纸条,凑向凸透镜,瞬间就把太阳火引来了,点燃烟斗,怡然自得地抽着。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打火机或是火柴,他撇着嘴,说天上有现
成的火不用,花钱买火是傻瓜!再说了太阳火点的烟,味道好!所以这部作品的开篇,我让辛七杂以这样的方式亮相。
辛七杂一出场,这部小说就活了,我笔下孕育的人物,自然而然地相继登场。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,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,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,开始与我度过每个写作日的黑暗与黎明!对我来说,这既是一种无言的幸福,也是一种身心的摧残。
伏
案三十年,我的腰椎颈椎成了畸形生长的树,给写作带来病痛的困扰。再加上更年期的征兆出现,满心苍凉,常有不适,所以这部长篇我写了近两年,其中两度因剧
烈眩晕而中断。记得去年夏天写到《格罗江英雄曲》时,我在故乡,有一个早晨,突然就晕得起不来了,家人见状吓坏了,不许我写作,说是命要紧,还是小说要
紧?我躺在床上静养的时候,看着窗外晴朗的天,心想世上有这么温暖的阳光,为什么我的世界却总遇霜雪?无比伤感。想想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,怀揣着各自不
同的伤残的心,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,多么不易!养病之时,我笔下的人物也跟着“休眠”,我能更细致地咀嚼他们的甘苦。
从
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树下》开始,二十多年来,我在持续的中短篇写作的同时,每隔三四年,会情不自禁地投入长篇的怀抱。《伪满洲国》、《越过云层的晴朗》、
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和《白雪乌鸦》等,就是这种拥抱的产物。有的作家会担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,我则没有。因为到了《群山之巅》,进入知天命之年,我可纳入
笔下的生活,依然丰饶!虽说春色在我面貌上,正别我而去,给我留下越来越多的白发,和越来越深的皱纹,但文学的春色,一直与我水乳交融。